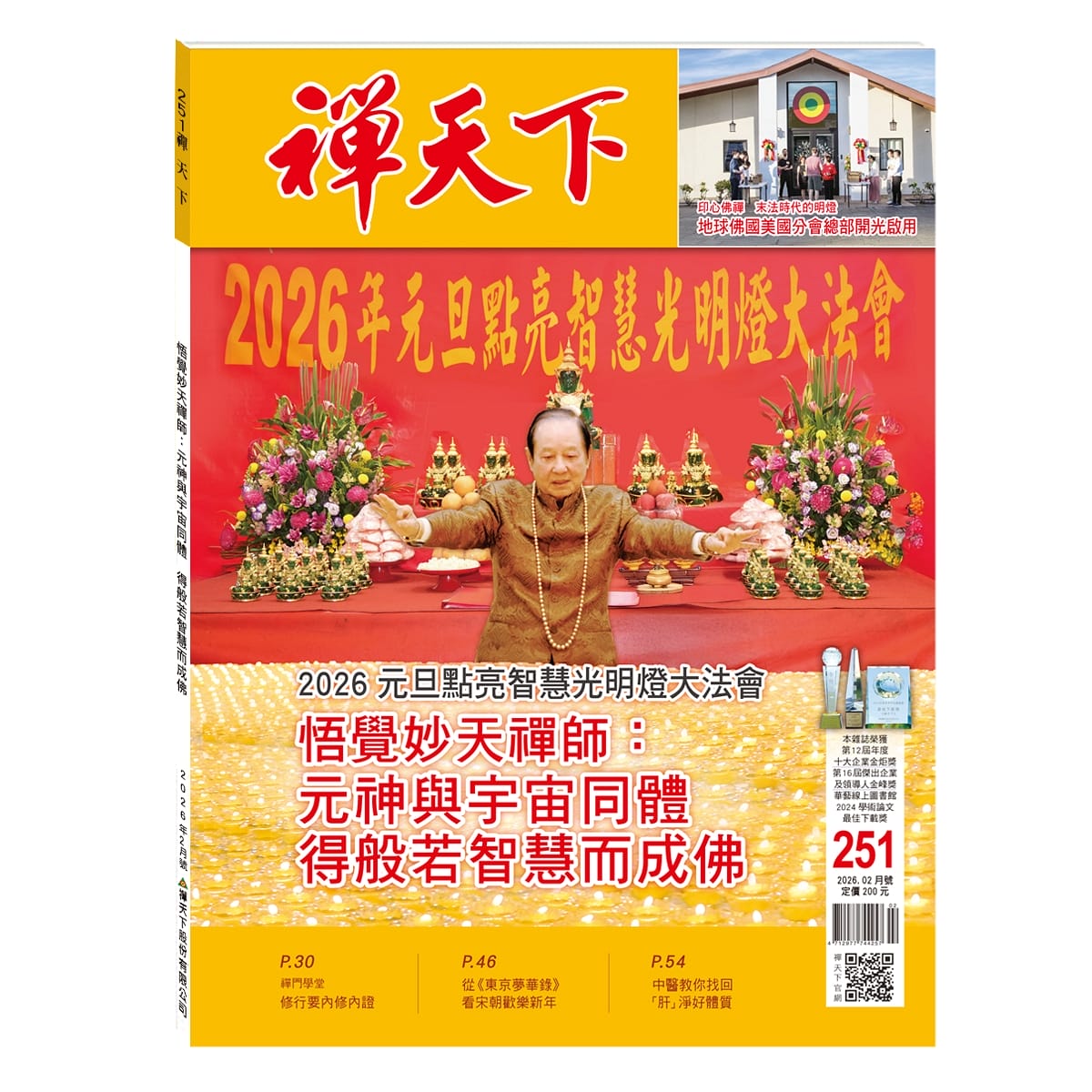文 / 黃馨儀 攝影 / 顏志倫
圖片提供 / 社團法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
「遊民」在台灣雅稱為「街友」,但由於遊民生活型態與主流社會迥異,加上居無定所、缺乏隱私,是「看得見的窮人」,故常成為社會維持公共利益下第一個被犧牲的族群,2003年SARS風暴席捲全台時,第一批被政府隔離的就是街友們。
為什麼會產生街友?台大社工系名譽教授鄭麗珍在研究報告中指出,長期失業、沒錢付房租、個人適應不良是淪為街友的三大主因。台大社工系名譽教授林萬億則表示,除失業之外,身心障礙街友通常是走失或被家屬遺棄,女性和年長者可能是被配偶、子女趕出家門,或為避免家暴選擇出走;也有部分街友是因身負前科,謀職不易,只能流落街頭。
「天生喜歡流浪的人是極少數,如果你跟著街友實際走一天,就知道那種生活一點也不好過。所以他們還是很希望有份工作,即便薪資很低。」長期關注遊民議題,曾被街友們封為「丐幫九袋長老」的林萬億如是說。
派遣+高房價=勞苦終日的漂流魯蛇
一般人總認為遊民是「懶惰的無賴」,卻不了解街友貧窮的背後真相。依據人安基金會統計,街友裡國中小學歷者佔61.5%,無一技之長者高達70.06%。由於欠缺專業,多數街友僅能靠做粗工、出陣頭、舉廣告牌…等零工餬口。有時遇到無牌人力公司,還會被苛扣薪資,不僅付出的勞力跟收入不成比例,受到職業傷害也只能自認倒楣。
「其實街友比我們想像的還更勤奮」,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郭盈靖表示,近9成的街友從前都曾有工作,其中甚至有1成曾是老闆。協會社工李宛真也指出,「很多人都認為街友遊手好閒,事實上有7成的街友會打工。但因為他們的工作屬於派遣勞動,每月薪資不到3,000元,根本租不起房子,所以只能流落街頭。」
令人憂心的是,由於產業結構改變、人力「億萬豪宅vs.居無定所」,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,更凸顯出「居住正義」亟待落實。派遣增加,造成「青年貧窮化」,加上政府無力遏止房地產炒作,使年輕卻陷入居住困境的「漂流魯蛇(loser)」日益增加。郭盈靖指出,過去的遊民多數屬老弱殘,但目前青壯年街友已占遊民總數近3成。若將借宿友人家、工寮等居無定所者計入,有工作能力的「隱性遊民」其實比想像中更多。而這也符合鄭麗珍指稱,有研究推估「遊民黑數是政府列管的10倍」的說法。
「這個社會最諷刺的是,當社會在為1坪200萬的豪宅讚嘆時,有些人卻連1坪的棲身之處都沒有」。郭盈靖擔心,一旦再度爆發類似2008金融海嘯的事件,或是社會支援系統中斷,「這些年輕的高風險群可能朝不保夕,有一天也會淪為街友!」
被忽視與歧視的弱勢
街友的存在雖然顯眼,但由於總體人數少、流動性高,導致街友在政治上成為零散且不確定的選民。也因為街友屬於「三不一沒有」的族群─人不多、問題不迫切、不構成威脅、沒有選票,政府通常不會以其為訴求對象。除非靠民間團體將遊民議題公共化,才會引發政府關注。
但因街友被社會大眾歸類為「不值得援助的窮人」,輔導街友難以獲得肯定,故協助街友的組織在台灣寥寥可數。民間團體在扶助街友的過程中,也常面對社區的壓力。「你們來幫忙是很好啦,但如果你們不在這裡,搞不好遊民會自動消失」,這類評語顯示社區將排斥遊民的心態「轉嫁」到公益團體上,也呈現出鄰里與公益組織之間的矛盾關係。
此外,街友也常被視為是「愛酗酒、會吸毒、有犯罪之虞」的族群。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方孝鼎解釋,街友之所以飲酒,多是為了驅寒不得不為之,或是為澆愁解悶、與同儕共飲而養成酒癮。所以酒癮通常是流浪的果,而非成因。林萬億則指出,台灣的遊民鮮少有毒癮患者,「毒品這麼貴,真正的遊民哪會有錢買?」
林萬億語重心長地表示:「街友被當成『都市之癌』其實是太誇大了,但社會對遊民的貶抑或忽視是事實。遊民各自有不同的生命經驗,又遭受優勢階級不同成分的歧視,這不是一兩天可改變的。不過在社福體系愈健全、社會包容性愈高的國家,人民淪為遊民的機會就會愈少。」
輔導街友 政府內部問題重重
如何輔導街友脫離困境?林萬億指出,社福體系必須包括緊急服務、過渡服務、穩定服務三者,否則很難奏效。
台灣民間團體由於資源有限,故多從事第一階段的緊急服務,提供衣食、醫療、盥洗、暫時性庇護為主,各縣市政府的遊民收容所亦屬此類。但因服務內容相似,彼此連繫不足、福利給付標準不一,導致個案遊走於各單位間尋求資源,使服務效果受限,甚至產生福利依賴,造成街友反而不易進入下一階段尋求脫貧的機會。
第二線的過渡服務,包含身心治療、教育訓練、協助安置。由於當中涉及大量資源的投入與整合,目前只能仰賴政府部門,但其中卻問題重重。首先,街友屬於「需要個別服務的流動人口」,政府跨部會、跨縣市合作的意願並不高,一旦涉及預算問題,各縣市政府便會將「戶籍地不明」的街友摒除於自家大門之外。而地方政府一邊要社會局輔導街友,一邊又要清潔隊丟棄遊民家當的行徑,更暴露政府各部門間缺乏整合。
此外,社工編制不足也是一大問題。以台北市為例,中正、萬華兩區的街友約有600人,台北市遊民專責小組成員僅有5位。社工每天上午面對數以百計的街友,下午還要處理行政工作與個案紀錄,有些社工自己都是派遣人力,飯碗朝不保夕,怎有心力個別輔導大量街友?
至於第三階段的穩定服務,則以提供「住宅」為關鍵。
「沒房子就沒門牌、沒信箱,也不能申請電話,這樣就算公司想錄取,街友也接不到通知」,熟悉街友困境的林萬億,一語道破住宅與就業間的連結。他表示,不論是社會住宅或房租津貼,都是可以讓遊民穩定下來的方法,但台灣受限於缺乏政策,導致社會住宅遲遲無法推行。不如學習美國,與小旅館或空屋屋主簽約,將房間分配給街友居住。之後請社工定期訪視,勞工局的交通車亦可定點接送至職業訓練班或求職面談處。如此一來,房東有錢,街友有家,政府也解決了問題。
郭盈靖則認為,台灣的社會住宅由於常與「弱勢」連結,周圍居民為防止房價下跌往往極力反對。事實上,社會住宅不一定要定位在「弱勢」,例如新加坡與香港就有高比例的公共住宅,以保障人民能「安居樂業」。而韓國將國家考試宿舍釋放為平價公共住宅的概念也值得效法,政府應出面將「蚊子館」與閒置空屋改建,讓年輕家庭或低收入者能以低價承租,而非每天想著要如何都更、土地活化。
治本仍須回歸法律與體制層面
住宅之外,協助街友最終仍須回到法律面。相較日本已於2013年制定全國通用的《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》,或歐美先進國家將街友問題向上游推展到住宅供給、所得維持與家庭功能等社政層面,我國仍停留在依《社會救助法》第17條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訂定遊民輔導辦法的狀態。
由於現行法規著眼於「社會救助」,以「戶籍制」為根本,不僅造成「有房、有門牌者有補助,窮到沒門牌的反而無法申請」的窘境,街友因直系血親有收入而無法請領補助的狀況亦時有所聞。可見現行法規脫離現實,亟待修正。
方孝鼎也指出,台灣因缺乏整體性、預防性的政策規劃,因此基層社工接觸到的街友多是長期流浪以致身心俱疲、關係斷盡、案底債務纏身的多重問題個案,即使投入資源,也不易回歸社會。這也使地方政府更傾向於花小錢提供餐飲、盥洗、寒冬庇護,避免街友死亡、髒臭;而非花大錢解決問題,輔導街友重生。換言之,中央政府的保守政策與立法,間接強化了地方政府「治標不治本」的取向。
除了修法,還要改變體制。芒草心慈善協會理事長張獻忠認為,雖然政府目前已有對街友的就業協助,但一旦他們失去工作,仍會再進入流浪的循環。「工作權無法受保障,等同生存權也遭剝奪」,郭盈靖與李宛真表示,若就業、住房等上游問題沒解決,不管花多大的預算,也無法減少街友。政府應管控非典型就業氾濫、房價炒作等問題,「伸出代表公共性的左手」,解決不公平的體制。
街友是一個人的財務狀況、居住結構、家庭關係崩壞到最後的產物,也是國家底層生態的縮影。參照已開發國家的經驗,經濟愈發展、階級兩極化會愈明顯,遊民數量與問題複雜度只會增加不會減少。2008金融海嘯後,全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「居住危機」,台灣的低薪高房價,也使年輕人擔心自己淪為街友的危機感變強。街友人數雖少,但問題難以根除,如何在向下沉淪之前拉他們一把,如何讓街友有尊嚴的活、有價值的活,進而回歸主流社會,在在考驗著政府的公共性與民眾的包容度。